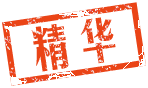|
|
欢迎访问西户网/西户社区网 XHUME.CC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会员

x
1957年7月,出生在陕西户县草堂镇城南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实验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演员,曾先后在《屠夫状元》、《拾黄金》、《顶灯台》等大小二十多出戏中担任主要角色,多次获得各种表演奖项。被观众称为“大西北黄金丑角”,香港评论界称其为“丑角慧星”,其表演诙谐、幽默,独具特色,雅俗共赏,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名丑孙存蝶:秦腔的卓别林
孙存碟在他的自传里写到: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命硬:我前脚出生,自然灾害、社会灾害就接踵而来;长身体时,碰到瓜代菜;长知识时,遇到文化大革命;想考大学,高考制度被废除;想找工作,又碰到上山下乡;找对象时,恰逢‘实行晚婚’;结了婚,又是‘一胎化’;好不容易进了城、端上铁饭碗,可人家又开始砸烂铁饭碗;厚着脸皮磨到今天,还面临下岗、待岗、分流的的危险。自从爬出娘胎,灾难始终未断,好像这一切都是由我捎带出来的。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孙存蝶的人生历程几乎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境遇,让人很容易想到路遥《平凡世界》里的那些人物,他们为了生存,奋斗、挣扎,演绎着一曲时代小人物的命运。还好,才情横溢的孙存蝶,从农村破茧而出,终于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蝴蝶,翩翩的飞舞在秦腔这个大舞台上,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彩,带给大家艺术的享受和欢笑。
没有高尚 只有真实
记者:你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为什么会想到去当秦腔演员?
孙存蝶:我只是中国亿万农民为了逃离贫穷、逃离土地中普通的一员。纯粹是为了进城,我才被逼上唱戏之路的,并没有别人认为的崇高理想,伟大抱负,只是觉得城市就是天堂,把农业户口变成吃商品粮就是进了天堂。
记者:你的长相,在传统观念里,可能离演员的标准比较远,是不是
曾经成为你当演员道路上的障碍?
孙存蝶:都嫌我丑,要不早就考上县剧团了。小时候我不但嗓子好,而且口琴、二胡、板琴都能弄。小学时,正闹文革,人家说要高大形象,嫌我丑,不要我。到了初中,户县剧团又来招人,又是因为我长得丑,不要。
记者:你又是如何当上秦腔演员的?一定经历了曲折?
孙存蝶:1975年。我高中毕业,由于高考取消,我通往城市的道路被彻底堵死,只好回到农村。这时,户县剧团又来招人,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
那时正值二三月,农村还很寒冷,村领导把门一关,前半夜开会,我站在窗外,冻得哆嗦,什么也听不见。第二天结果一出来,推荐的是村长的娃,大队长的娃和大队长的侄女,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在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一早晨。早饭时,已经鼻青脸肿。父亲说:“娃,别哭了,农村也是活人的地方。”
饭桌上,我对父亲说:“不是说推荐和选拔结合吗,我自己去选拔,选不上,再回来当农民。”父亲一听很高兴,桌子一拍:“我娃高中没白上!你考上了,我再给村长做工作。”
走到半路,我心里还是很犹豫,担心人家不让我考。这时,正好碰到一个肩上扛着锄头的住队干部,他看见我,放下锄头,对我说:“先到镇上考,回头我给村长说。”有了父亲和住队干部的鼓励,我才有了去考试的勇气。到了以后,才知道来考试要有推荐信,没有推荐信的我在会议室外踌躇着。门忽然打开,是一个老师出来上厕所,后来知道这个老师叫向恒禄,他让我进去坐着。我进去后,坐在角落里,快到下班了,人也快考完了,也不敢吭声,向老师说你不是考试嘛,上来!
我一上去,亮开嗓子唱了段《海港》选段。才唱了几句,老师就说这娃嗓子咋愣好,可惜就是形象不好。问我还会乐器不?我又吹了笛子,拉了段二胡,算是过了初试。一回家,我就趴在父亲耳边轻轻地说:“今天考上了!”一周后,复考通知来了,要我去县剧团复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候在人山人海的县剧团外,等到我上场了,因为嗓子高,让乐队调到G调后,开口唱道:“我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老师说,考了一个上午,还没有这么好的嗓子。然后又一阵踢腿,翻跟头,终于看到主考在我名字上圈了个红圈。我高兴的一口气跑了30里,回到家又趴到父亲耳朵边小声说:“今天又考上了!”父亲还是那句话,吃完饭好好劳动,继续等通知。第三次,县上的亲戚把通知送了回来。这一次,是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干部主考,几千人最后才定30多人。最后一次是在剧场舞台上考,我还是表演了原先的那些。记得那天大雪纷飞,我是跌着跟头流着鼻涕回到家的。一周后,正式通知书一大早就来了。父亲说:“这下是真的了!”。然后领着我到村长家,对村长说:“我娃考上了,如果你不给娃开证明,我就死了算了!”没想到,村长一点也没为难我们,直接给开了大队证明,我就这样到户县剧团正式学艺去了。
记者:你考到了户县剧团,但后来却去了甘肃武山县剧团?
孙存蝶:我在县上学了两年,但户县剧团不给我办粮户关系,也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一心就想农转非,就想成为国家职工。刚好甘肃那边说是能解决这一切问题,我就去了。
武山“发迹”之地
记者:武山让你有了归属感吗?
孙存蝶: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甘肃武山县恢复剧团要在陕西招演员,当时户县剧团有2个半小时的节目,一个半小时是我演的。连夜把我叫到户县招待所,让我去武山考试。
记者:你是怎样到的武夷山?
孙存蝶:我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布包包,包里装的冷红苕和蒸馍,是我路上的口粮,兜里揣着20块钱,去那里的火车单趟9元1角,再加上到西安的班车5毛,还剩下吃饭钱。
火车凌晨5点到武山,火车站离县城还有5里路,我走到武山剧团,找到曹团长家。我说我就是演员孙存蝶。他疑惑的看着我,让手下把我打发到城乡结合部4毛钱一晚的车马店住宿。晚上洗漱时照镜子才发现,原本又瘦又丑的我,经过长途劳顿,显得更丑了,难怪团长看我不像演员。为了考试的时候有力气,我步行到县城的国营食堂,花了3毛5吃了碗肉面,又花2毛8吃了碗素面。领我去住宿的2个人正到处寻我,“下午考你!”
我回到车马店,先把行头拿来,到了剧团,还是没有人正眼看我,甚至有的人斜卧在乒乓球案子上。一段秦腔下来,人们的眼珠子往中稍微移动了点,卧的人慢慢坐起来。再一段陕西快书下来,躺的人坐正了,我又来了普通话绕口令,迷糊剧,大家看得很兴奋,团长问:“你还有啥?晚饭到我家吃,行李拿来,改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团长才告诉我,和我一起考试的有十几个人,担心有人冒充孙存蝶,在县上五大班子面前丢人,让我下午提前考。晚上,我把下午那一套重新表演了一遍,孙县长说:“看了几回演员,就这一个。”第二天,团长把准迁证、粮票证明放到了我的手上。
记者:终于吃上商品粮了,当时是啥心情?
孙存蝶:从村子出来,走到半路,我转过身,指着村子说:“南城寨,
我今天离开你就不想回来了!”
记者:在走上成功福地,后来是怎么回到陕西的呢?
孙存蝶:我在武山一呆就是8年,成功的扮演了《十五贯》里娄阿鼠这个角色。因为演得好,经常借调到天水市。一开始到天水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天水是个城市,离西安也近。1985年,我参加“甘肃省首届青年大奖赛”,在兰州得到文化厅厅长的赞扬:“戏曲界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演员!”要求我比赛这五天每天都要参加,天水不要回去了。于是,我被调到了甘肃省青年剧团。1988年,在没有得到团里同意的情况下,我跑到西安参加了陕西台的“西北五省首届戏曲大奖赛”,拿了一等奖。1989年,因为回老家,在同学家住着,碰到原来在户县剧团的老师,叫我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唱2场戏,结果因为观众欢迎,又演了一个礼拜。院长说:“别回甘肃了!”我就这样,又干了三年临时工。
记者:又如何算是正式回到陕西?
孙存蝶:三年的临时工作,主要是甘肃那边不放人。戏曲研究院每年都派人去甘肃办手续,但那边就是不同意。1992年,甘肃文化厅的厅长、艺术处处长来到陕西,最后一次叫我回去,给了我很多许诺,但我还是拒绝了。很巧的是,就在那个时候,广西文化厅的人也住在那里,他们是来叫张艺谋回去。最后这边给我重新上了一套手续,我才算正式调了过来。
记者:为什么你很在乎临时工?
孙存蝶:因为是临时工,我又特别勤奋,练功的时候经常叫人欺负和嘲笑,连院子里的狗都欺负我,为此,我还打了几个人。1992年我打算卷铺盖走人,领导才急了。也因为这,我的关系问题才得以迅速解决。
记者:小时候,你在农村生活特别贫困,到了城市,生活是不是就变
好了呢?
孙存蝶:我在1986年、1987年和1988年这三年,生活很不好。一周才能吃一顿干面。周末在家正做面,来了朋友,老婆问:“咋办?”我说改吃面片。正做着,又来一个朋友,老婆又问咋办,我说再加一瓢水。
记者:你现在还回过武山吗?
孙存蝶:我去过兰州,现在上台30分钟下不来。
恨多爱少谁来逗我笑?
记者:你把欢乐带给了大家,在生活里,你是否也是个快乐的人?
孙存蝶:我并不像舞台上看上去那样快乐。不得不说,我的性情里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恨多爱少,就是明证。
记者:对于今天这样的好生活,那你有幸福感吗?
孙存蝶:但说实话,我并不快乐,也不幸福。我的任务是把欢乐带给大家,把痛苦留给自己。
谁又来逗我笑呢?在我的生活里,没有笑声、幸福和快乐。做人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只花了我20%的精力,80%的精力都在做人上了。但直到现在,50岁的人了,还不会做人,觉得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比如出去演出时,闲了大家爱打麻将、挖坑,而我一点也不爱。我喜欢看书,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看书,现在那些著名作家的书,我都读过。特别喜欢阎连科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亦庄梦》。
我做人的原则是“同流不合污,崇洋不媚外,传统不保守”。
记者:有传媒报道,在2006年底,你在青华宫正式皈依道教?法号浪荡子?
孙存蝶:我和道长飘牙子很投机。我是没有家庭观念、单位概念的人,爱到处浪。朋友招呼一声,就提个兜兜到北京,到美国、法国演出去了。因为师父叫飘牙子,我就叫浪荡子,全世界的浪。
记者:道教和秦腔有关系吗?
孙存蝶:秦腔原本就是广场文化、庙坛文化、佛道文化形式吸收进来的,逐渐形成系统,戏曲是民间艺术集大成者,历代艺人呕心沥血共同的结晶。正如有人说的那句:“百姓的乱弹,演变出和尚的唱经,道士的叹唱,幻变成民间的道情。”
记者:如何看待你的生活工作?
孙存蝶:妻子和我是同行,她能理解。而我除了演戏,什么都不会干,对生活一窍不通。连电褥子都不会开关,更不要说其他事情。和妻子一路走来,打仗、骂架,甚至闹过婚变,但我这辈子认“穷死不离婚,亏死不打官司”的死理。
戏如人生不可游戏人生
记者:你也开始写书法并爱写戏如人生?
孙存蝶:戏如人生,但不可游戏人生。人生如梦,不可在梦里求生。
我坚持“本本分分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原则。虽然对现状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但我还是会在艺术阵地忍耐和坚守。
记者:在秦腔不景气的现实情况下,你却有戏接不断,而且连去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国际友人都来请你演戏?
孙存蝶:戏曲来源就是田间地头、民间的,我个人没发现秦腔的低潮。自打我爱上、干上秦腔,我就感到秦腔有影响力,但也没发现什么时候出现过高峰。反正我一直忙碌着,铺地毯似的演出,从没停歇。
记者:你对现在艺人低龄化现象如何看待?
孙存蝶:首先,我没看到艺人低龄化。有部电视剧叫《小孩不傻》,
其实观众也不傻,一时的红火不是代表一世。
记者:很多戏曲演员最后都放弃了戏曲,改投影视或者流行歌曲这些流行文化,你为什么还一直坚守在秦腔这个古老的千年舞台?
孙存蝶:秦腔是自古迄今稀有的一门与灵魂有关的事业,亦是未来人类文化事业的一个准则。我从事的是人类“大乐”与“大礼”的事业,至死我也不后悔。我要做一个秦腔阵地的守望人。我认为,新老秦腔艺术家都应该有把秦腔戏唱到美国百老汇去的雄心。这是我的“雄心”,也是我的“野心”。
一生都把灵魂交给舞台
记者:你的成功从武山开始,你觉得自己能够成功,应该归功于哪些因素?
孙存蝶:我觉得自己遇上了几千年一遇的好机遇。那时文革刚结束,社会等待文化复兴。
其次是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传统急需找到新的传人。其三是在国民经济还没找到出路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民族瑰宝拿来“晾晒”。文革后,没有什么艺术形式比戏曲更快捷、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心灵悲怆。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入武山剧团,并成功扮演娄阿鼠这个角色。这是时代发展的悲剧,却也是我个人奋斗的喜剧。戏曲在我心中升华为具有清晰目的的“个性展示”,并想倾全部心智和想法改变传统戏曲的规范与程式。我的生相特点促进了我的愿望,我的嗓音条件成全了我的追求,我所处的武山小城的贫穷落后完美了我的个性化戏曲风格。可以说,一个人的“发迹”,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能少。
记者:你怎样认识丑角这种角色?
孙存蝶:我的戏曲观念里,戏曲是演给穷人看的。艺术是平民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做人民的演员。丑角,揭示的是生活固有的荒诞,虽然生活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荒诞的只能说是我们的眼睛。而我的丑角所创造的荒诞,是没有骄傲、逗趣的。我理想的丑角境界,不是高枝上可以炫耀的哪一种东西,只能是看不见、摸不着,浑身都是刺,还蛮鲜艳。就像叫做“毒药”的香水。
记者:你怎么认识丑?
孙存蝶:我对观众的承诺是:孙存蝶绝对丑,不丑不要钱:真丑,绝对不佯装丑态、故作嗲情。丑出自然,丑出朴素、丑出哲学、丑出美学、丑出质量、丑出深度、丑出硬度,同时还要丑出固有的可笑和无奈。丑是美的底肥,丑是“臭氧层”。我丑,秦腔美,是为遗憾里的幸事,是为绝望处的天光。我愿让观众眼睛放射的光芒照亮我的丑角艺术。
记者: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你如何处理雅与俗、市场与艺术的
关系?
孙存蝶:让拿捏装腔走开,把“高度深沉”留给哲学家,让“现代”“新潮”走开,把“急功近利”留给商人。
记者:你很小的时候,就被村里人成为戏魔,你成名后的自传又叫了《戏魔》这样一个书名,怎么解释戏魔这个说法?
孙存蝶:就是把灵魂交给舞台。戏不是戏,戏是灵魂,戏是生命。这也是最高级和最终的艺术方法。俗话说“台上三秒钟,台下三年功”,你觉得唱戏除了需要这样坚韧吃苦的练功精神外,灵魂和肉体都必须双倍交代给舞台。真功夫需要的岂止是三年磨练,还需要一生的灵魂体验,持久保持朴素本色和对万事万物的热爱。
记者: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孙存蝶:2008年,我才50岁,我想重新考虑我的人生和艺术座标。如果是60岁,打算回老家,盖一个草棚,需要生活费时出去唱点戏挣点钱。 但我现在还没做,所以新的打算还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化蛹成蝶 题记
他,出身寒微。但他似乎比数以亿记的中国那一个时代的农民幸运,他,一个乡村苦孩子凭着自己倔强与顽强的意志、超人的本领敲开了秦腔之门,并且在中国戏剧舞台有了一席之地。
他作为一名娱乐大众的人物,却并不是博人一笑的纯粹小丑,他不仅代表着中国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大众文化,更代表数以万记的丰富心灵。
从乡村到城市,从贫穷到富有,从默默无闻到妇孺皆知,他艰辛的奋斗同样成熟了自己多彩人生。
2008年第一个月古城西安迎来了五十年不遇的一场大雪。雪,粉饰了寒冬里有些满目疮痍的城市,而这一天,我们终于在与城墙隔阂相望的一个宾馆的四楼里见到著名秦腔丑角孙存碟。
刚刚步入他的工作室门口,恰巧孙存碟匆匆下楼,“快上楼”孙先生热情的招呼道。很快采访在他还算很大的办公室里开始。
他端把椅子,一下子坐到办公室中央,一个大茶杯就放在脚下。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看了一下午精彩“脱口秀”表演,时间在孙存蝶生动的讲述中愉快的飞逝。即使讲到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听起来都是令人愉快的。我惊讶于他口才的好,表情滑稽可笑,语言妙趣而幽默,通俗而不媚俗,这也正是他的表演艺术特点。“哭出来的笑声”和“笑出来的眼泪”,他看起来和舞台上没有太多的区别,分不清是戏里还是戏外,只有不停打进的电话,他耐心的解释、安排,才让我们感到他的缜密与热情。
我们无意窥视这名在秦腔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内心世界。
1998年,当他带着独特的诙谐和绝技出现在京津舞台。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快乐,更多的是人们开始对秦腔这门艺术的思考,对这种有着独特和顽强的生命力的艺术的另眼相看。大西部北、大秦腔、秦之声,唱起来,吼起来。那是龙的子孙,龙的吼声,在稳定与变升中海涅。
人民时报1998年12月17日,第7版评论员文章称“艺术只有回到人民中去,才堪称艺术。著名作家陈考英撰文《秦丑孙存碟晋京启示录》中作为我国戏曲丑角行当的一次个人专场演出和专题研讨活动,此举受到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对当前仍处于低谷之中苦苦徘徊的戏曲艺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秦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呈现为一种开放的体系,每个时代它都从姊妹艺术中吸取大量的营养。在丑角行当实现这种“新的综合”,孙存蝶堪称有心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将眉户、豫剧、黄梅戏、京剧等姊妹剧种中富有喜剧特色的艺术手段融入其秦丑表演体系之中,通过有机融会,孙存蝶对秦丑表演体系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性的“新的综合”。
孙存蝶的戏曲喜剧表演风格展示了一位成熟的喜剧艺术家对稳定性与变异性、“杂”与“一”、“融”与“化”、“形”与“神”等艺术辩证法的探索,显示了秦腔丑角巨大的艺术张力。他的艺术实践和广大观众对其实践的认同雄辩地证明,丑角艺术必须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市场意识和改革的紧迫感,自觉地实行自我更新,实现“新的综合”,才能真正走向市场,为民族戏曲的振兴添砖加瓦,鸣锣开道。
20年来,孙存碟仍是孙存碟,也许是关中腹地男儿血脉使然,从“发迹”的甘肃省武山县到省城兰州,又从兰州率性的回到阔别8年的故土长安、风风雨雨一切世俗在他面前苍白无力,而孙存碟的世俗却唤回了人们心中久远的童真,还是很久的某些东西。
当社会都成了票友,只有我是观众,程蝶衣说。
戏如人生,孙存碟说。
三年半的临时工,三年半的黑人黑户,一次次的“诙谐”终于使自己有了合理的身份和一席之地,以反常的作为来达到正常的愿望是人和社会关系的是合理与荒谬。那个时候,连剧院里的一只狗都无视我,孙存碟说。
孙存碟是江湖的,只有江湖才会有大师,孙存碟是大众的,只有泥土才会孕育惊艳。
孙存碟又是性情中人,他的人生、爱情都在嘴上,他的人生又是锋芒毕露,率真、本真的人生,这样的性格具定了要付出代价的,从回到陕西的那一天起,18年间获奖无数。他为秦腔赢就了掌声,也为政府和官员赢得光彩。他的戏一直从农村的大舞台唱到了“梅花奖”的颁奖现场,却得不到单位行政领导的认可。
有人说孙存碟的成功,是陕西秦腔的失败,甚至一人出名,全省丢人。也有人暗示他要世故些,甚至要他与官员作陪。他捉摸不透,演员就是要凭自己的演技,而不是处世的演技。
岁月如大浪淘沙,但淘不尽孙存碟的说艺,他仍然独立于舞台之上。
我们不难理解18年在官员视线之外的荒诞。
如果说当初走出八百里秦川是为了寻找归属?而对于孙存碟这样一个人恐怕永远注定了漂泊。
艺术上的强者,生活上的大智若愚,用戏为生命添加意义,用超越虎空之上的剧情,去安慰陷在虚空当中的人,如果说人生如戏,就不难理解他为何遁入道门。
我问他,你幸福吗?你快乐吗?这几乎是我数年来访问时最后一笔必答题。
“我不幸福,我不快乐”,他浓浓的关中方言,静静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就在我再次迷惑时,他却一笑了之。
“为何要皈依道教”,我仍追问秦腔来源了,宇宙文化、道教文化,我回到道教有什么不好?
“为何要法号‘浪荡子’”?
“我四处漂泊,你说叫什么好?”他那种一晃即逝的顽皮何狡黠,我的目光再次和他相遇。
两个小时的访问,逼近傍晚,还有一场演出在等他,窗外的雪覆盖了古城,城市的另一边演出就要开始,我们握手道别。
文章来源于网络
|
|